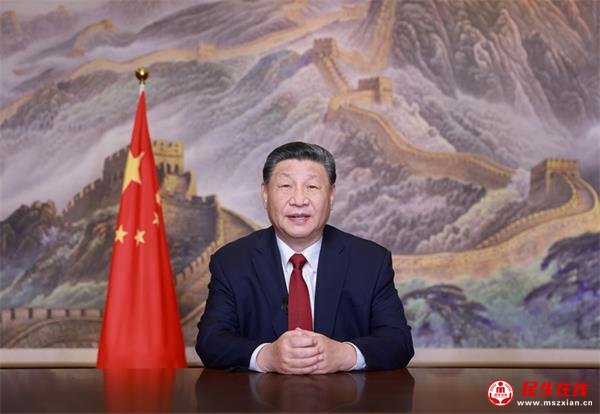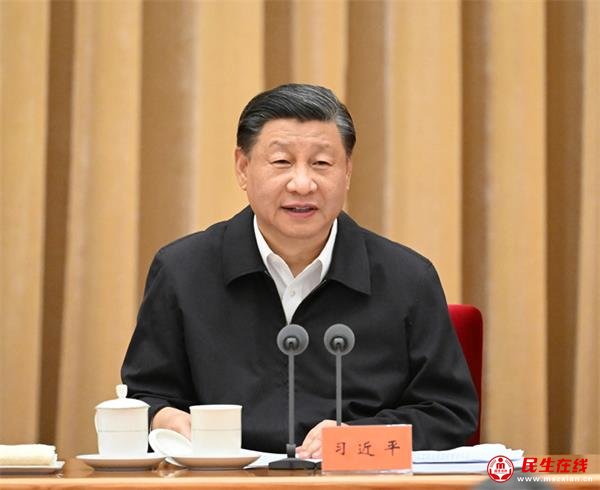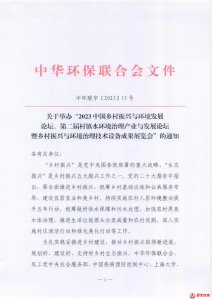|
“没想到一次电鱼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会尽力补偿,弥补我犯下的罪行。”在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法庭上,非法捕捞案被告人陈某全低着头,声音沙哑地说。随着判决被告人缴纳的生态损害赔偿金44万汇入专用账户,这场牵动长江上游生态保护神经的案件,终于迎来了生态修复的新篇章。 案件回溯:24尾鱼引发的连锁反应 2023年12月30日晚8时,陈某全、桂某银等人趁着夜色,划着皮划艇,带着电瓶和逆变器悄悄来到复兴镇的赤水河上。几个头灯的光在黑暗里闪烁了一阵,随后“啪——”的一声,电流划破水面,原本静谧的水域泛起阵阵涟漪,一大片鱼翻着肚皮浮上水面——这是他们精心策划的非法捕捞行动。 他们一直忙活到第二天凌晨4时,被巡河的渔政部门当场查获,人赃俱获。 “当时就想着冬天鱼好抓,用电鱼设备能多捞点,根本没考虑后果。”桂某银在庭审时懊悔不已。他们或许不知道,头灯光束下那几尾鳞片闪着金属光泽的岩原鲤,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鱼类,更是赤水河生态链的“晴雨表”。 那天晚上,他们非法捕获了24尾野生鱼。经鉴定,除了岩原鲤,这批渔获还包括白甲鱼、宽口光唇鱼、厚颌鲂、中华倒刺鲃、唇鲭、粗唇鲍等8个品种,总重为12884.2克。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评估报告更令人心惊:这次非法捕捞造成直接损失达40741.2元,间接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不低于407412元。 “电鱼不仅直接杀死鱼类,还会破坏它们的繁殖能力,甚至影响藻类、底栖生物等整个水生系统。”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飞告诉记者,“赤水河作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避难所’,任何一点破坏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为了保护这些珍稀特有鱼类,从2017年开始,赤水河在全国率先开始试点全面禁渔,并一直执行至今。 案发后,赤水市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4人提起刑事诉讼,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赔偿生态环境损失。法庭上,当公诉人展示岩原鲤野外种群数量持续下降的监测数据时,陈某全等人的表情从满不在乎变成了震惊。 最终,被告人陈某全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个月。被告人桂某银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被告人简某平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被告人胡某树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限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陈某全、桂某银、简某平连带赔偿水生生物资源价值损失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共计444153.2元。 修复之困:跳出“放流即修复”的思维定式 44万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应该怎么用? “如果只是简单判罚和增殖放流,这起案件就失去了典型意义。”赤水市人民法院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法庭庭长钟宇在谈及案件审理难点时说。 传统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多以放流普通鱼苗为主,但赤水河的特殊性让法官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赤水河自2017年全面禁渔以来,普通鱼类种群已显著恢复。“若继续大规模放流普通鱼苗,可能导致物种竞争失衡,反而挤压岩原鲤、圆口铜鱼等珍稀鱼类的生存空间。”刘飞告诉记者,“圆口铜鱼、长鳍吻齁等珍稀鱼类种群恢复仍然缓慢,生存前景不容乐观;长江鲟、胭脂鱼目前仍未发现野外自然繁殖迹象,灭绝风险依然存在。” 法律条文为创新生态修复方式提供了支撑。钟宇援引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20条第1款规定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找到了新的使用方向:“原告请求修复生态环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对于包括珍稀特有鱼类在内的野生动物种群繁育、受损栖息地重构等系统修复保护工作,具有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等特点,由被告自行履行修复义务并不现实。此时,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宜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采取替代性修复方式开展相关修复工作。”钟宇说。 法庭最终决定,将444153.2元赔偿金用于更系统的生态修复,而非单一放流。 这一决定起初引发争议。“为什么不直接放鱼?”有人曾提出质疑。钟宇耐心解释:“就像给病人治病,不能只补充维生素,还得修复五脏六腑。岩原鲤需要的是适宜的产卵场、干净的水质和安全的食物链。” 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以往惯例,将赔偿款上缴遵义市政府,不一定能“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才能“专款专用”,让生态赔偿款的使用更加科学合理?钟宇解释说,增殖放流鱼苗作为重建种群规模的方法,仅仅是科学保护珍稀濒危水生物种的重要措施之一。“对于人民法院而言,在个案审理执行中,不仅需要考虑受损鱼类在品种、数量上的填补,更应关注受损珍稀特有鱼类所处流域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以及生物资源的系统恢复,变传统单一增殖放流修复方式为构建水生态系统、立体、科学修复体系。” 为确保修复方案的科学性,法庭主动联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带我们实地勘察时发现,案发水域的卵石滩是岩原鲤天然产卵场,但因水流冲刷导致卵石分布不均。”钟宇回忆,“这才明确了修复方向——不仅要‘补鱼’,更要‘修场’。” “这也补齐了环资审判中对生态修复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使用用途存在的认定模糊粗放等短板,提高了司法修复工作的严肃性和实效性。”钟宇说。 司法+科研:构建珍稀鱼类的“立体防护网”
图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司法保护与科学研究中心挂牌。赤水市人民法院供图 2024年春,全国首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司法保护与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赤水河畔挂牌。当陈某全等人的赔偿款以“司法认领”形式汇入专用账户时,一场“精准修复”战役正式打响。 “这笔钱将分三路发力。”刘飞介绍,一是统筹用于赤水河流域珍稀濒危水生生物科学繁育、种群监测、增殖放流等渔业资源保护修复事项;二是建设人工鱼巢、人工鱼礁、补植复绿等栖息地修复工程;三是集中开展科普、法治宣传及场所建设。
图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司法保护与科学研究中心的赤水河长江鲟司法培育池。张浪摄 记者在中心实验室看到:人工繁育池内,首批岩原鲤幼苗已孵化成活;院子里的大水池里,一批“青少年”岩原鲤正蓄势待发,等待放流。而在河谷深处,人工鱼巢、人工鱼礁已布设完成,为珍稀鱼类重建产卵场。这些数据会定期反馈给法庭,形成“司法监督—科研实施—效果评估”的闭环。
图为在中心实验室,刘飞带领科研助理护鱼进行时。张浪摄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对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威慑。“这起案件在当地引起轰动,并作为遵义市2024年长江十年禁渔典型案例被通报。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类似的案件数量明显下降,2021年的时候,一年还有30—40起类似案件,而今年上半年只有6起。”钟宇说,这正是这一典型案例的深层意义——让生态环境保护从法律条文走进人心。 “这种创新解决了珍稀特有鱼类司法修复的科学性、专业性、技术性问题,为包括水生、陆生、鸟类在内的野生动物司法修复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样本,实现了‘办理一案、修复一片、治理一域’的良好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钟宇说。 |